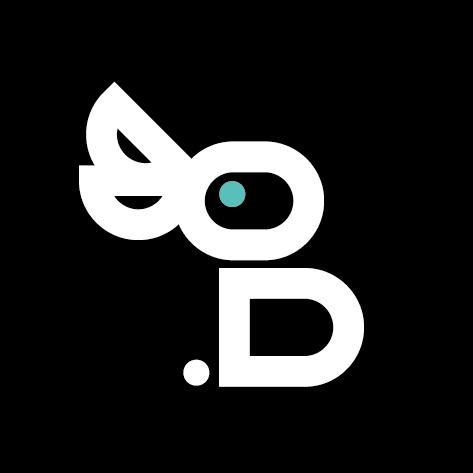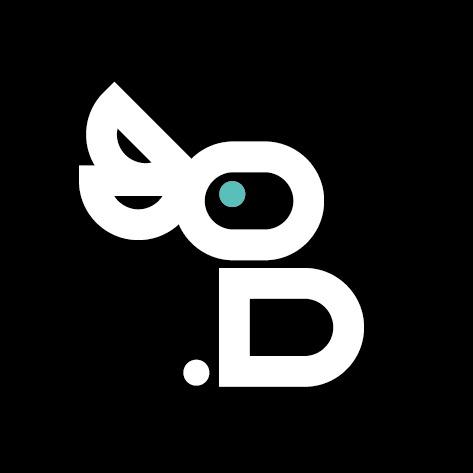让神经科学回归弗洛伊德,意识不过一种感觉?

在马克·索尔姆斯(Mark Solms)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痴迷于宏大的存在主义问题: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是什么造就了如今的我们?后来,他开始学习神经科学,却很快发现神经心理学对关于心灵的这些开放式问题没什么耐心。作为一位新晋科学家,索尔姆斯做了件闻所未闻的事情,他把弗洛伊德认作神经科学之父,并开创了一个新领域——神经精神分析学。
索尔姆斯在人生道路上还遇到过另一个障碍。他出生于纳米比亚,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长大。后来,索尔姆斯于一家医院工作,该医院位于索韦托,那里的军事占领者试图镇压抗议者。“一完成学业,我们就得被迫入伍,伤害那些曾经照顾过的人。”他说道。“这种事,我在情感上没法承受。”于是,他逃往英国,在那里接受了精神分析培训。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他才回到南非。
影响深远的童年创伤
索尔姆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协调脑科学和生活经验研究。如今,他在新书《隐蔽源泉》(The Hidden Spring)里提出了自己的意识理论。索尔姆斯认为,神经心理学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意识。“智力诞生于大脑皮层,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意识也源自那里。”索尔姆斯写道,“我不同意。意识远比这更原始。它诞生于人类和鱼类共有的那部分大脑。这就是书名中的‘隐蔽源泉’。”这本书是对现代神经科学的一次深入探讨,对我们如何思考、做梦、记忆和感知做了惊人解释。
我联系到了索尔姆斯,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他一直待在南非开普敦。我们讨论了脑——心智问题、神经心理学的偏见,以及家庭创伤如何塑造了他的人生历程。

你写过你童年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你哥哥遭受了严重脑损伤。你能描述一下发生了什么吗?
索尔姆斯:那时我四岁,他六岁。我父母在划游艇,我在水边,但他和一些朋友爬上了俱乐部屋顶。然后,他被绊倒,从三层楼跌落到下面的人行道上,头骨骨折。在撞击过程中,他失去了意识并且经历了持续性脑出血。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所以我们必须将他空运到开普敦的一家医院。好在他在事故中幸存了下来。让我感到不安和极度难以理解的是,他虽然看起来跟以前一样,但又完全变了。他失去了他的发展里程碑,比如,变得大小便失禁;他的人格也不同了,变得更加情绪化、易怒和难缠;他的智力水平也变了。
你说这对你产生了深远影响?
索尔姆斯:的确如此。这场意外让我开始思考,大脑怎么可能只是他脑袋里坏掉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他会变成这副熟悉而又陌生的样子?他去哪了?这个人,我的哥哥,怎么会是一个器官呢?我迅速地推及自己,然后想,“嗯,我是我的大脑吗?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我的大脑受损,我会变成另一个人吗?原来的那个我会去哪呢?”而这件事对于我父母来说是一场悲剧。他们为此感到极度内疚。

所以当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在问一些当今神经科学所涉及的深奥问题了。什么是自我?大脑如何与我们的精神体验联系起来?
索尔姆斯:我觉得,我只是因为那件事过早地陷入这些思虑。对我来说,这些问题也与死亡有关。如果我的肉体死了,我就会消失,这太可怕了。我还想到,如果我们会永远消失,那做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想法让我非常不安,将我推入一种只能被称为“抑郁”的漩涡里去。我还记得那些早晨的感觉,“上学有什么意义呢?”以至于我都没有力气去系上鞋带。显然,我不相信在四五岁时我就决定了成为一名神经科学家,但如今回想起来,这两件事必然有关联。成为神经科学家,大概算是解决那种虚无主义绝望的一种方法。印象中,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过,唯一真正值得做的事情是努力去理解存在是什么,感受性(sentience)又是什么?
“神经精神分析”的诞生
你继续研究神经科学,尤其是梦的科学。这对你思考意识的本质有什么影响?
索尔姆斯:神经科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心灵与大脑如何关联,所以神经心理学是神经科学中最吸引我的领域。但当我来到大学,我学到的是些抽象功能——记忆、语言、知觉和执行控制的信息处理机制。人们对心灵的实际主观存在没有兴趣。当我问起关于“记忆的内容”和“人的生活的内在驱动力”的问题时,我的教授们严肃地劝告我:不要问这样的问题,这对你的职业生涯不利。
你有一个重大发现,推翻了我们只在快速眼动(REM)睡眠期间做梦的主流理论。你发现了什么?
索尔姆斯:主流理论只是假设:当快速眼动睡眠停止时,我们的梦也会停止。但我发现,大脑中负责引起REM的部位受损的病人仍然会继续做梦。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自己犯了重大的方法论错误,这种错误就是不收集主观数据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对科学来说,处理梦的实际主观体验是件尴尬的事,这就是我的教授们说“不要研究那些东西”的原因。但如果我们遗漏掉一半的可用数据,就会错失一些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重要信息。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你对弗洛伊德的兴趣非同寻常。你实际上受训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之后还编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全集。
索尔姆斯:对,我的同事们都吓坏了,他们告诉我这是伪科学。其中有一个对我说:“你知道吗,天文学家不研究占星术。”的确,精神分析已经失去了它的根基。弗洛伊德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神经科学家和神经病学家,但在后来的几代研究者中,精神分析丧失了生物科学根基,所以我能够理解一些人对精神分析的不屑。但值得称道的是,它研究的是真正的心灵体验,而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也是神经心理学缺失的东西。于是我转向精神分析,尝试系统性地研究主观经验,并推断其背后的机制。
我们误解了弗洛伊德吗?他是否有被我们忽视的科学洞见?
索尔姆斯:很有可能。我不会假装弗洛伊德没有犯过一些重大错误,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是一位先驱,迈出了系统性研究主观经验的第一步。他之所以没有在神经科学上取得大的进步,并放弃了这一领域,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事物。即使是脑电图,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广泛应用的。所以,当时没有研究活体大脑活动的方法,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拥有的方法了。但他基本的观察总结,是占据中心地位的情绪——情感感受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很大。这就是精神分析的本质所在,即我们的理性、逻辑和认知过程如何被情绪力量所扭曲。

你开创了“神经精神分析”这个新领域。这种方法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索尔姆斯:我所学的神经心理学也可以说是神经行为主义。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1984年的著作中指出,神经心理学是令人钦佩的,但它排除了心灵,即活跃的心灵主体。这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我想要把心灵重新带回神经心理学。在上世纪80年代的神经心理学中,情绪尚未被研究。而情绪在心灵体验中的中心地位,以及隐藏在情绪背后的东西,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驱力”。简单来说,他的观点是,不愉快的感觉代表了未被满足的需求,相反,愉快的感觉则代表满足了的需求。这就是了解“我们如何满足自己最深层生物需求”的方式。这种观点为认知提供了一种基础,而我认为这种纯粹又简单的基础在认知科学中是非常缺乏的。
意识是一种感觉
意识科学领域存在着巨大争论。解释大脑和心灵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科学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大脑由神经元和突触连接组成,而心灵涉及思考和感觉的非物质世界,它们似乎存在于两个完全独立的领域。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索尔姆斯:主观经验,即意识,当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具身的生物,是经验的主体。所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大问题。我们可以说,想象物理器官如何成为经验主体是极端困难的,所以它们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宇宙,因此主观经验是不可理解的,它在科学范围之外。但我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我赞成的一种观点是,一定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弥合这种分歧。
其中争论的主要焦点是意识是否能够还原为物理或生物学规律。哲学家大卫·查尔莫斯曾推测,意识是自然界的基本属性,无法被还原为任何自然规律。
索尔姆斯:我接受这个观点,除了“基本”这个词。我认为,意识是自然界的一种属性,但不是一种基本属性。这很容易解释。很久以前发生过一次宇宙大爆炸,过了很久之后,生命第一次出现。如果查尔莫斯认为意识是宇宙的基本属性,那么意识一定早在生命诞生之前就存在了。我知道有些人相信这一点。但作为一名科学家,当我们看到这些证据的分量时,“甚至在宇宙大爆炸之时,就已经有了意识的某种基本形式”的说法,就不那么可信了。“基本属性”这个说法,基本上等同于上帝,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你当然可以发现大脑功能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各种关联。我们知道大脑损伤——比如发生在你哥哥身上的事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这仍然无法解释因果关系。就像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说:“大脑是如何跨越从电化学到感觉的鸿沟的呢?”
索尔姆斯:我认为,我们把人类意识作为所谓意识的模型,是把这个问题困难化了。(塞尔)这个问题听起来更奇妙。所有这些思考、感受和哲学思辨怎么可能都是脑细胞的产物呢?不过我们应该从感觉这种更基础的意识雏形开始讨论。即把意识看作只和存在价值有关的东西:生存是好事,死亡是坏事。这是所有生物的基本价值体系。糟糕的感觉意味着我不太好——我很饿、很渴、很困,我受到生命存亡和肢体受损的威胁;而好的感觉则有相反的意味——当前状况有利于我的生存和繁衍。
你是说意识本质上是关于感觉的,而非认知或智力。
索尔姆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从意识最基本的形式开始讨论”更有助于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一个物质生物怎么会拥有意识这种神秘又奇妙的东西呢?把意识简化为更生物性的东西,比如基本的感觉,然后我们才能开始在之上构建复杂性。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我感觉”,之后才有了问题:这种感觉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感觉是关于什么的?然后我们有了最初的认知——“关于这一事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于是,感觉延伸到了知觉,以及世界上有机体的其它认知表征(representation)上。

感觉、意识与记忆
这些感觉源自大脑的什么地方?
索尔姆斯:感觉起源于大脑中一个非常古老的部位——脑干上部,这个部位是我们和所有脊椎动物共有的。大脑的这个部分已经有5亿年的历史了。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这些结构的损伤——在网状激活系统的某些部分中,小到火柴头大小的损伤——会使所有意识消失。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更复杂的认知意识依赖于上脑干产生的意识的基本情感形式。
所以我们把过多注意力放在了大脑皮层上,我们赞美它,因为它让人类变得聪明。
索尔姆斯:确实。人类对自身在演化中所处的位置感到骄傲:唯独哺乳动物拥有宽阔的大脑皮层,而我们人类的大脑皮层面积甚至更大。这是我们在意识神经科学史上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关于大脑皮层是意识来源的证据非常薄弱。如果你把一只新生哺乳动物——比如一只小鼠——去皮质化,它不会丧失意识。它不仅早上会醒来,晚上去睡觉,它还会跑来跑去、挂在栏杆上、游泳、吃东西、交配、玩耍、把幼崽抚育养大。所有这些情感行为离开了大脑皮层依旧存在。
人类也一样。生来就没有大脑皮层的儿童,被称为脑发育不全性脑积水(不要和脑积水混淆),与我刚才描述的这些实验动物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早上醒来,晚上入睡,高兴时微笑,沮丧时大吵大闹。当然了,我们没法跟他们讲话,因为他们没有大脑皮层。他们不能告诉我他们有意识,但会像我们的宠物一样表现出意识和感觉。
你是说我们确实有两个大脑——脑干和大脑皮层。
索尔姆斯:是的,但大脑皮层本身无法产生意识。可以说,大脑皮层从脑干中借用了意识。此外,意识并非大脑皮层所固有的。大脑皮层可以进行高水平且独特的人类认知操作,比如阅读理解,而根本不需要意识。所以为什么我们还会有意识呢?答案是我们需要感觉来进行认知,因为这是价值的来源。事情进展得好还是不好?所有选择、所有决策,都需要建立在一个价值体系中,建立在一物优于另一物的价值观之上。
所以思维是什么呢?我们还能谈论思想的神经化学(本质)吗?
索尔姆斯:思想的最基本形式关乎选择。发生在我们日常的心理生活中的大部分认知过程,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如果我们不需要做出选择,那么万事自然发生。而现在我面临着两种选项,我需要选择其一来行动。意识让我们能够做出那些选择,因为它提供了价值判断。换句话说,思考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直到我们碰见了不确定的局面,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我们需要感觉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忆是如何融入意识的?
索尔姆斯:一切认知的基础成分就是我们拥有的记忆。感觉印象进入我们的记忆并留下痕迹,我们便可以通过认知的形式重新激活它们,并以各种复杂的方式重新组合,包括提出新的想法。但认知最基本的结构就是记忆痕迹,而大脑皮层就是一个巨型表征仓库。所以我刚才说,本质上认知并非都具有意识,只是在说,很大一部分记忆都是潜藏在意识之下的。我们不可能对一生中接收的数以亿计比特的信息都有所意识,所以有意识的部分是那些从长期记忆的巨型仓库中提取而来的短期工作记忆,但它们只是所有记忆之中微小的一部分。
你说记忆的功能是预测我们未来的需求。而海马体,我们常说的大脑的记忆中心,是用来想象未来以及储存过去信息的。
索尔姆斯:从过去事件中学习的唯一目的,是更好地预测未来事件,这就是记忆的意义所在。它不仅仅是个图书馆,来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归档。我们需要记录过去的事件,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以其作为基础,来预测未来。是的,海马体对于想象未来和回忆过去一样重要,你也可以说这是在回忆未来。
一门真正的意识科学、关于主观经验的科学,难道不能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思想和记忆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大脑中吗?
索尔姆斯:当然能。这就是为什么我比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更认真对待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他们会问,为什么史蒂夫在他人生这个阶段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大脑中的神经元是如何产生这一切的?我是说,如果从最基本的因果机制出发,我们只是在谈论一种感觉,而它们在普通的生物学术语中并不难理解。接下来,要厘清所有那些基于我们整个生活的认知——我怎么去满足我的情感需求?与此同时,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地预测和感受问题,并试图解决它。
这就是神经精神分析的前提。解释大脑中发生的生物学现象是一条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通过心理学的解释——也许我需要一位心理治疗师,来帮助我理解,为什么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中会冒出一个特别的想法。
索尔姆斯:你刚刚概括总结了我的整个科学生涯。我认为两种道路我们都需要。当初驱使我去研究神经科学的,正是这些非常重要又有趣的问题,这些塑造了我的生活的复杂事物,是如何与我的身体器官相关联的?你知道的,在医学院或研究生课程中,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必须丢掉那些好奇心与神秘感,丢掉对那些宏大问题的兴奋和痴迷。而由于我的个人经历,我无法放弃对这些问题的好奇。这就是我做这些事的动机。
作者:Mark Solms | 封面:Anxo Vizcaíno
译者:王两 | 校对:Sixin
编辑:山鸡 | 排版:平原
原文链接:https://nautil.us/issue/98/mind/consciousness-is-just-a-feeling